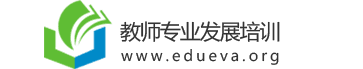问题

赵彦彪提问
1个回答
浏览:48次
2022-12-18 15:24
以序观文———《阿Q正传》序的副文本性解读
引 言“副文本”作为“正文本”的辅助性文本而存在,是相对于作品 的“正文本”而言的,比如文本中的标题、序跋、注释、附录等都属于“副文本”的范畴。副文本“参与文本意义的生成和确立; 副文本 是理想读者阅读正文本的导引和阈限,是阐释正文本的门径( 或陷阱) ; 副文本为正文本提供视界和氛围( 或遮蔽) ,是正文本的文学生态圈乃至历史现场”① 。《阿Q正传》的第一章作为小说文本的 “序”,为其后“正文本”( 从第二章开始) 的阐释提供了“门径”。
鲁迅做小说“力避行文的唠叨,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,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”②,那么他又为何在《阿Q正传》中将论述较为繁琐的“序”作为小说的第一章呢? 仅仅是为了插 科打诨式地切“开心话”的题吗? 显然,此“序”用于传达“意思”。第一章的“序”是鲁迅写作《阿Q正传》这篇小说的一种策略性的安排,是我们理解《阿Q正传》“正文本”的“门槛”,为我们理解作者意图、解读文本意义提供了重要的提示和阐释的氛围。
关于鲁迅小说的“序”,以往研究多关注《狂人日记》的文言序与白话正文的反讽叙事,而对于《阿Q正传》之序的研究也多集中在序的反讽性的研究论述上,即鲁迅在序中看似遵循了传统传记的写作套路,实际却是一种调侃、戏谑,从中透露出强烈的反讽意味。实际上,从小说的“序”的副文本性角度出发,我们也应该看到《阿Q正传》的“序”对于解读文本的人物设置、作品风格和小说主题的辅助性的意义所在,“序”在作品的阐释中发挥着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。
序中的叙述已表明传主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,即阿Q是一个集合性的概念。由此进入正文本,我们就不难理解文本第二章中的阿Q的“‘行状’也渺茫”③之类的话了。阿Q在未庄活动,然而他在未庄没有家,只是暂时借住在未庄的土谷祠中。不仅如此,阿Q在未庄生活,在未庄里却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,人们只在需要有人来帮忙做工时,才会想起阿Q,甚至连做工时也可以不需要阿Q的参与,因为阿Q的活动完全可以被小D之类的人替代。阿Q没有紧密的社会性、社交性,阿Q在未庄这一社会集体中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。没有具体指涉,除了“无”的含义外,还可以理解成所指涉的对象是广泛的、普遍的。
传主所指的普遍性,在鲁迅自己的言说中也有证可寻,鲁迅要“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,一下子就推诿掉,变成旁观者,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,又像是写一切人,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”④。由此看来,鲁迅在《阿Q正传》的序中,看似繁琐无意义的论证,其实是一种策略性的安排: 表面上按着作传名目、立传通例、传主名字、传主籍贯等,遵循着传统的作传体例为阿Q作传,似乎能够呈现出一个具体的人物形象,实际上一步步的“刻画”,却导向了人物形象更加的模糊不清。这种模糊性的描写,其目的就是让读者摸不着在写谁,从而作为旁观者来看正文中所描写的阿Q是如何的自尊、自大和自负,因为无具体所指,进而疑心写的可能是自己,由此开始反思自己。
鲁迅用阿Q所指涉的这些读者,首先是指阿Q这个阶层的人,比如正文中的“未庄的人”“酒店里的人”“他们”……都是如阿Q一般的人。这些人生活在受压迫的社会最底层,他们生活困顿,只能寄托于让“服从”来营造虚无缥缈的安宁,一旦有机会,他们也想做主子,也想满足自己的兽欲。此外,阿Q的集合性概念还指涉阿Q们的主子们,阿Q们身上的奴性和缺点,这些统治者们同样也具有。所以说鲁迅用阿Q所指涉的,是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的性格特征,是辛亥革命时代中国社会中人们的普遍性格缺点。
然而,在当时的社会中有阿Q们的存在,那么换个时代呢? 这也是鲁迅先生的担忧: “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,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,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,而是其后,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”⑤。想到《阿Q正传》这篇小说在今天的不朽性,不免要惊恐和无奈,惊恐于,我们嘲笑阿 Q,我们自己也是阿 Q,我们嘲笑阿Q的欺软怕硬、自欺欺人、自负自大,反观自我,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
从序中得知,阿Q的形象是群像,是“混合照相”。“阿 Q”是一个集合概念,反映当时中国国民的集体特征,由此进入正文,一探这一群像的特征。阿Q最大的特征,便是尽人皆知的“精神胜利法”了,这种自欺欺人的精神上的胜利,文本中显示为从自我欺骗、自我麻木到通过打自己而获得胜利感的发展。阿Q企图通过自欺来掩盖被打的事实,他自己被打,却想象着世界是多么不像样,竟然被自己的儿子给打了,通过贬低打他的人来获得自欺欺人的安慰,从而感到心满意足。此外,他还自比“状元”的“第一名”之“第一”,为自己成为“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”⑥而感到自豪。当只靠想象麻木不了自己,并且也化解不了失败而带来的苦痛时,他开始“行动”,通过打自己两个嘴巴,来解气,获得心平气和的感受,仿佛打的不是自己。
阿Q除了惯用“精神胜利法”外,他还自负、自高自大,常常将“我们先前——比你阔的多啦! ”⑦ 、“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! ”⑧ 等话挂在嘴边。他不仅倚仗无依据的过去来显耀自己,还靠虚无的以后来获得自豪感,由此他便自认为了不起,自认为见识高,“所有未庄的居民,全不在他眼睛里”⑨。阿Q们不知变通、较为顽固,以自己乡下人的标准,来判断城里人的所作所为,将自己没见过、没听过、没接触过的事物视为有悖常理,是错误的。他们认为“长凳”不能叫作“条凳”,葱段不能被切成葱丝,没见过的煎鱼也是不合他们乡下人的标准的。阿Q们攀比心极强,暗自认为有些人低自己一等,所以这些人连捉虱子也不能比自己捉得多。阿Q们仗势欺人,仗着“名人”的“口碑”来抬高自己,可笑的是所倚仗的竟然是被“名人”教训这样的事。阿Q们欺软怕硬,打不过王胡、假洋鬼子这类人,就只会欺负处于相对弱势的小尼姑。阿Q们在思想上极为保守、封建,他们固守封建礼教,将人本性的男女之爱理解为“异端”,将本能的性需求解释为“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”。
阿Q的这些特征,是鲁迅先生在当时社会中的人们身上所体察到的,这些劣根性,是从许许多多的“个”中发现的普遍性。“阿Q主义”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称谓,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劣根性的集合。虽然历史不会重复,但会惊人的相似,这种“阿Q相”具体到“个”,也许不会重复,但是在本质上会惊人的相似。也就是说,历史发展到今天,不论是在中国的社会中,还是在世界的哪个地方,还是会从群体中发现阿Q的一些特性。鲁迅先生看到的“阿Q们”是跨越阶层、超越时代的,他观察人事是从人类本质出发的,他对于社会的反思、批判与启蒙,也是从探寻人类本质的深层次出发的。
然而,在宏大的英雄叙述模式中,写的却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人物,或者说,是在平凡之下的一种人物。显然,所谓的英雄是一个假英雄。在序中看似一本正经的分析之中,却掺杂了种种不确定的因素。又因为传主的平凡无奇,连传的名字都取自“闲话休题言归正传”之中,蕴含着戏谑和正话反说的意味。同样地,正文的各章标题,看似有恢宏气势,若关照到各章内容之中,气势便轰然倒塌。所谓“记略”,不是对历史上著名的史实的叙述,而是著名的相反一极,记述的是平淡无奇甚至是有些可笑、可供嘲讽的一些小事,比如阿Q自高自大,看不起旁人,欺软怕硬,攀比惹事等事情。所谓“优胜”“革命”“大团圆”等,都可反其意来理解,在这表面的堂皇之下,皆是一些捉襟见肘的事,如所谓的“优胜”,不过是自欺欺人的“精神胜利法”。
序中论证立传名目的严肃性和实际论述中的调侃性,形成一种反讽的意味,这一方面为理解正文内容定下了反讽的基调,提供一种戏谑的解读氛围,即用与表面的叙述相反的思维来看小说中的故事;另一方面,这种戏谑味道与第二章以后“正文本”的反讽风格共同构成一个整体,形成《阿Q正传》反讽性的文本氛围。
文本的反讽性不仅体现在结构的安排上,还有语言上的显现。比如标题中的用词,所谓“中兴”,通常情况下,指的是国家层面的意义,指国家由衰退到复兴。而鲁迅将“中兴”一词用在阿Q身上,可谓是夸大了阿Q的身份地位,再联系到阿Q的“中兴”,实际上不过是做了一些偷盗之事,由此满是讽刺戏谑的味道。又如结局的“大团圆”,不是阿Q爱情之树的开花,也不是阿Q生计问题的解决,更不是阿Q革命的成功,而是阿Q之死,这与所称的“大团圆”之意义大相径庭。
阿Q的“恋爱”也不过是阿Q自己臆想的夸大化。所谓恋爱,于阿Q而言,根本就是空洞的词语存在,仅仅是“我和你困觉”⑩的本能性欲的初步表达,更不用说阿Q的“恋爱的悲剧”了。恋爱都是虚无缥缈的,又何来的悲剧呢? 同样地,所谓阿Q的“革命”,也是一种本能欲望的表现,与革命本身的严肃性完全不符。在阿Q一流的眼中,革命不过是改朝换代,换了个主子罢了。“革命”的成功,对于他们而言,仅仅意味着奴才造反成功,奴才成为了主子,意味着自己的欲望( 财欲、性欲) 能得到尽情的满足。而“革命”的行动,在阿Q们的认知中,也仅仅是“站队”和“剪辫子”一类的事。将严肃宏大的“革命”一词放在阿Q们的肤浅的理解之中,集庄严与可笑于一体,造成荒唐滑稽的效果,形成反讽的语言氛围。
“阿 Q‘先前阔’,见识高,而且‘真能做’”瑏瑡,作者在文本的叙述中,为“先前阔”“真能做”等话语加上了引号,这不能不引起注意,如果阿Q真的“先前阔”“真能做”,那叙述语言中的引号岂不是多余? 显然,这是一种反语的语言表述安排: 阿Q先前并不阔,阔,只是阿Q自己精神上的幻想; 阿Q也不是真的能做,他更不“几乎是一个‘完人’”12
此外,《阿Q正传》中叙述人称的设置也显露出一定的反讽意味。序中的叙述者是第一人称的“我”,“我”在遵循着传统的作传体例,一板一眼地寻找为阿Q作传的名目,搜寻阿Q的姓氏、籍贯、名字等身份信息。这些显然与“否正统而倡异端”13的鲁迅的行为相悖,因而可以说,是“我”而不是鲁迅,在为阿Q作传寻找名目。在服从传统的作传形式之中,隐含的是语义相反的含义。鲁迅在序中所探究的问题都是在正话反说,表面上是在为阿Q作传寻找名目,探究阿Q的姓氏和籍贯等问题,但是实际上考究来考究去,其结果竟然是关于阿Q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,均不可考,唯一能确定的只有阿Q名字中没有任何含义的“阿”字。作传人旁征博引地要证明阿Q的不朽之处,结果证明的却是阿Q的平平无奇,其中满是反讽和戏谑的味道。
再者,“我”自己声称不是一个“立言”的人,而作传讲究的是名正言顺,作传人都不能“立言”,那又何谈传主的威严、传记的名义呢? 在序中叙述者( 作传人) 声音明确,要为阿Q立传,竭力证明为阿Q作传的合理性和必然性。然而进入从第二章开始的“正文本”后,“我”隐而不见了。在“正文本”中,“我”不再引导读者做评判,而是一方面让读者与阿Q拉开距离,让读者自己处于判断的位置看阿 Q,看到阿Q的可笑之处; 另一方面,因为阿Q的无具体指涉性而让读者疑心写的是自己,从而进行自我反思。
其实,不论是在结构上的反讽,还是在人物话语、叙述话语中的反讽,其反映的都是一种文化和生存上的反讽与反思。阿Q当然不会真正地要去革命,他都不知道革命真正意味着什么,其革命的真实动机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。对于阿Q们来说,革命是另一种生存方式,他们想做主子,因为他们看到主子们可以三妻四妾,主子们拥有充足的物质。阿Q们所理解的革命全在“物质”层面而与“精神”无涉,这何尝不是更深层意义上的反讽!
鲁迅作《阿Q正传》,并不是在浅层面进行思考与批判,而是深入社会现实与人类本质中去思考问题的,他批判国民的劣根性,呼唤“个”的觉醒和团结奋斗,同时他也在反思时代、历史与现实的革命状况。
体会到“序”中的这种批判和颠覆态度,进入“正文本”,就不难理解鲁迅在“正文本”中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判。鲁迅先生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,主要体现为对阿Q的性格特征的揭示、暴露,比如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、欺软怕硬、自负自大、仗势欺人、思想封建等。此外,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揭示与批判,还体现在阿Q们对于革命的态度与认识上,阿Q认为杀革命党、杀头“好看”,阿Q所理解的革命就是释放自己的性欲,让自己的私欲得到满足。
鲁迅通过描写群像性的阿Q形象,来表达对于整个国民性的批判。当时的社会中有不少人,都是“阿 Q”,他们不知道革命到底意味着什么,以为革命就是改朝换代,换个新主子来服从,或者是“穿着崇正皇帝的素”的反清复明,要不然就以为是与他们毫不相关的新派的活动,又或者仅仅意味着剪辫子这种头发上的外在变化。鲁迅以一个先觉者的敏锐,察觉到了中国国民性格的这种愚昧无知,他写出阿Q相,并对此进行批判,但是又不仅仅在于批判,如果止于批判,只能算是无谓的牢骚。
带着“序”所体现的批判态度,进入对“正文本”的阅读与阐释之中,不难理解,鲁迅的批判并非无源。其批判是在对现实社会状况的反思中,所生出的由衷的“怒其不争”。《阿Q正传》中对革命的表现与描写,是鲁迅先生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深切感受,是对辛亥革命等历史事实的体会与反思。鲁迅不仅揭露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,而且也在深层次中揭示了导致民族的劣根性的根源,关乎中国内外,这种国民的劣根性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。
封建的统治在于维护封建帝王的权威和统治,这就忽视了人之“个人”的存在,几千年的仁义道德深入国民内心,让阿Q们深信之而力行之。因为太顽固,所以深受其荼害而不觉,这就“培育”出了阿Q们的“阿Q相”:顺从、顽固、贪婪、自欺、自负、封建……然而在特殊的历史时代,在帝国主义与外族的压迫和剥削中,我们民族被激起的不仅有反抗的意识,还有奴隶和奴隶之奴隶的顺从意识。他们苟活于封建统治者和异族的剥削与压迫之下,服从成疾,患上严重的劣根性,现出奴隶相。
阿Q们对于“革命”的认知,仅仅停留在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式的改朝换代的层面上。革命的行动于他们而言,也无非是剪不剪辫子之类的事情。认知多一些的,如小说中的阿 Q,想要脱离奴隶角色,进入主子的位置上,却始终认识不到人作为个体的“个性”的存在。所以这多出的一些认知,也只是一种“奴隶道德”的体现。
鲁迅憎恨阿Q身上的劣根性,但是“哀其不幸,怒其不争”。鲁迅“对于中国善良的质朴的底层人民,是具有无比的热爱的。他愈爱他们,对于他们所遭受的失败与失败主义的毒素便愈加憎恶、愤怒,宛如一个慈爱的母亲,对于她无辜的儿子头上长着恶疮所起的恶情感一样”16。他写出沉默的国民性的魂灵来,暴露出阿Q们的服从与奴性意识,他所要争取的是“人各有己,而群之大觉”17。
鲁迅先生用历时和现时的眼光来关照历史与现实,关注阿Q们的精神“优胜”。所谓启蒙与觉醒,是思想上、精神上的觉醒。鲁迅先生希望阿Q们觉醒、不再自欺,成为有个性、有 理想的“个”,“个”之团结一致,共同对抗侵略者的剥削。要唤起“群之大觉”,必须暴露、痛击“国民劣根性”,阿Q们必须在思想上换新,因而“首在立人”。
鲁迅在批判与反思之深处,有“哀其不幸”的同情,也有“怒其不争”的愤懑。存在,如何在反人性的环境中生存? ———“是故将生存两间,角逐列国是务,其首在立人,人立而后凡事举; 若其道术,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。”18鲁迅不仅是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者,也是新的国民性的建构者。辛亥革命时代的中国人所缺乏的,是人作为“个”的“个性”。阿Q们没有自我的意识,缺乏反抗、战斗和前进的精神,他们处在封建统治者和外族的压迫之下,麻木而妥协、顺从。
阿Q们的顺从和“精神胜利”,其后果只能是伤害了他们自己,至于压迫、剥削他们的“主子”,则不会伤到毫发。鲁迅痛定思痛,致力于改变中国国民的这种生存困境,其主张的,正是人之“个性”与“精神”的建构。
阿Q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,受着压迫和凌辱,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,生活没有基本的保障。鲁迅虽“怒其不争”,不免也“哀其不幸”,对他们抱以同情。阿Q是鲁迅所处时代各个阶层的奴隶根性的性格的集合,是具有群像特征的人物,鲁迅在《阿Q正传》中要揭示其身上的劣根性,然而其最终目的并不在暴露,而是要唤醒。如果人各有己,每个人都有反抗的意识,那么集体就会有一致对抗侵略和压迫的力量。
鲁迅思考的出发点远高于对具体环境中的国民性的观察,他是从人类生存的层面出发而反思自身存在的。因而如果要具体到中国,具体到中国的辛亥革命时期,鲁迅的这些思想足以烛照中国的前途与未来,为混沌的中国社会指明方向。鲁迅从人类、民族生存的角度出发而进行思考,阿Q们如果能够觉醒,坚持反抗与战斗,这就是“个性”的获得,而群之“个性”精神崛起,“立人”的目的也就达到了。
结 语《阿Q正传》的“序”作为进入正文文本的“门径”,一方面为我们理解正文内容提供了解读氛围,序中传主身份及文本叙述的模糊性,指涉正文文本中人物阿Q的集合概念性,序中表现出来的反叛传统的态度,暗示了正文文本的反讽风格; 另一方面“序” 也与“正文本”的叙述形成互相指涉的跨文本解读关系,“序”和“正文”表达的反讽和批判不是唯一的目的,鲁迅先生在《阿Q正传》中所显示的,还有对于历史与现实的反思,以及对于“立人”理想的追求与呼唤。对于《阿Q正传》来说,“序”是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部分,它为后面的正文文本奠定了一个基调,是理解正文文本的密钥。
鲁迅做小说“力避行文的唠叨,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,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”②,那么他又为何在《阿Q正传》中将论述较为繁琐的“序”作为小说的第一章呢? 仅仅是为了插 科打诨式地切“开心话”的题吗? 显然,此“序”用于传达“意思”。第一章的“序”是鲁迅写作《阿Q正传》这篇小说的一种策略性的安排,是我们理解《阿Q正传》“正文本”的“门槛”,为我们理解作者意图、解读文本意义提供了重要的提示和阐释的氛围。
关于鲁迅小说的“序”,以往研究多关注《狂人日记》的文言序与白话正文的反讽叙事,而对于《阿Q正传》之序的研究也多集中在序的反讽性的研究论述上,即鲁迅在序中看似遵循了传统传记的写作套路,实际却是一种调侃、戏谑,从中透露出强烈的反讽意味。实际上,从小说的“序”的副文本性角度出发,我们也应该看到《阿Q正传》的“序”对于解读文本的人物设置、作品风格和小说主题的辅助性的意义所在,“序”在作品的阐释中发挥着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。
一、模糊的群像——从序看“阿Q”
所谓《阿Q正传》之阿 Q,听起来实有其人,然而细究起来看,不论是在小说故事的论述中,还是在小说所指涉的现实中,阿Q这个人物并非确切地有所指,而是许多人的性格的集合,其指涉范围可广至中国,甚而全世界、各个时代。
鲁迅在《阿Q正传》的序中,着力为阿Q立传寻找一个“名正言顺”的理由,然而论述来论证去,结果竟然是能确定的只有名字中的“阿”字。至于作传的名目、立传的通例、阿Q的名字如何书写、阿Q的籍贯等问题,均不可考证。《阿Q正传》名义上为阿Q这个人作传,然而却找不到实际存在的人,可以说《阿Q正传》是一篇没有传主的传记。换言之,没有,在某种意义上也并不代表着无,而是具有一种普遍性的意义,我们可以将阿Q的具体所指理解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一群人、整个社会的人,即阿Q的所指是具有社会涵盖性的。“阿Q”是一个集合概念,集合概念反映集合体的某些特征,“阿 Q”的概念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普遍的特征,尤其指性格方面的———中国国民的劣根性。序中的叙述已表明传主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,即阿Q是一个集合性的概念。由此进入正文本,我们就不难理解文本第二章中的阿Q的“‘行状’也渺茫”③之类的话了。阿Q在未庄活动,然而他在未庄没有家,只是暂时借住在未庄的土谷祠中。不仅如此,阿Q在未庄生活,在未庄里却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,人们只在需要有人来帮忙做工时,才会想起阿Q,甚至连做工时也可以不需要阿Q的参与,因为阿Q的活动完全可以被小D之类的人替代。阿Q没有紧密的社会性、社交性,阿Q在未庄这一社会集体中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。没有具体指涉,除了“无”的含义外,还可以理解成所指涉的对象是广泛的、普遍的。
传主所指的普遍性,在鲁迅自己的言说中也有证可寻,鲁迅要“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,一下子就推诿掉,变成旁观者,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,又像是写一切人,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”④。由此看来,鲁迅在《阿Q正传》的序中,看似繁琐无意义的论证,其实是一种策略性的安排: 表面上按着作传名目、立传通例、传主名字、传主籍贯等,遵循着传统的作传体例为阿Q作传,似乎能够呈现出一个具体的人物形象,实际上一步步的“刻画”,却导向了人物形象更加的模糊不清。这种模糊性的描写,其目的就是让读者摸不着在写谁,从而作为旁观者来看正文中所描写的阿Q是如何的自尊、自大和自负,因为无具体所指,进而疑心写的可能是自己,由此开始反思自己。
鲁迅用阿Q所指涉的这些读者,首先是指阿Q这个阶层的人,比如正文中的“未庄的人”“酒店里的人”“他们”……都是如阿Q一般的人。这些人生活在受压迫的社会最底层,他们生活困顿,只能寄托于让“服从”来营造虚无缥缈的安宁,一旦有机会,他们也想做主子,也想满足自己的兽欲。此外,阿Q的集合性概念还指涉阿Q们的主子们,阿Q们身上的奴性和缺点,这些统治者们同样也具有。所以说鲁迅用阿Q所指涉的,是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的性格特征,是辛亥革命时代中国社会中人们的普遍性格缺点。
然而,在当时的社会中有阿Q们的存在,那么换个时代呢? 这也是鲁迅先生的担忧: “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,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,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,而是其后,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”⑤。想到《阿Q正传》这篇小说在今天的不朽性,不免要惊恐和无奈,惊恐于,我们嘲笑阿 Q,我们自己也是阿 Q,我们嘲笑阿Q的欺软怕硬、自欺欺人、自负自大,反观自我,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
从序中得知,阿Q的形象是群像,是“混合照相”。“阿 Q”是一个集合概念,反映当时中国国民的集体特征,由此进入正文,一探这一群像的特征。阿Q最大的特征,便是尽人皆知的“精神胜利法”了,这种自欺欺人的精神上的胜利,文本中显示为从自我欺骗、自我麻木到通过打自己而获得胜利感的发展。阿Q企图通过自欺来掩盖被打的事实,他自己被打,却想象着世界是多么不像样,竟然被自己的儿子给打了,通过贬低打他的人来获得自欺欺人的安慰,从而感到心满意足。此外,他还自比“状元”的“第一名”之“第一”,为自己成为“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”⑥而感到自豪。当只靠想象麻木不了自己,并且也化解不了失败而带来的苦痛时,他开始“行动”,通过打自己两个嘴巴,来解气,获得心平气和的感受,仿佛打的不是自己。
阿Q除了惯用“精神胜利法”外,他还自负、自高自大,常常将“我们先前——比你阔的多啦! ”⑦ 、“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! ”⑧ 等话挂在嘴边。他不仅倚仗无依据的过去来显耀自己,还靠虚无的以后来获得自豪感,由此他便自认为了不起,自认为见识高,“所有未庄的居民,全不在他眼睛里”⑨。阿Q们不知变通、较为顽固,以自己乡下人的标准,来判断城里人的所作所为,将自己没见过、没听过、没接触过的事物视为有悖常理,是错误的。他们认为“长凳”不能叫作“条凳”,葱段不能被切成葱丝,没见过的煎鱼也是不合他们乡下人的标准的。阿Q们攀比心极强,暗自认为有些人低自己一等,所以这些人连捉虱子也不能比自己捉得多。阿Q们仗势欺人,仗着“名人”的“口碑”来抬高自己,可笑的是所倚仗的竟然是被“名人”教训这样的事。阿Q们欺软怕硬,打不过王胡、假洋鬼子这类人,就只会欺负处于相对弱势的小尼姑。阿Q们在思想上极为保守、封建,他们固守封建礼教,将人本性的男女之爱理解为“异端”,将本能的性需求解释为“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”。
阿Q的这些特征,是鲁迅先生在当时社会中的人们身上所体察到的,这些劣根性,是从许许多多的“个”中发现的普遍性。“阿Q主义”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称谓,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劣根性的集合。虽然历史不会重复,但会惊人的相似,这种“阿Q相”具体到“个”,也许不会重复,但是在本质上会惊人的相似。也就是说,历史发展到今天,不论是在中国的社会中,还是在世界的哪个地方,还是会从群体中发现阿Q的一些特性。鲁迅先生看到的“阿Q们”是跨越阶层、超越时代的,他观察人事是从人类本质出发的,他对于社会的反思、批判与启蒙,也是从探寻人类本质的深层次出发的。
二、反讽———以序看风格
《阿Q正传》的“序”不仅在阿Q这个人物的解读上与“正文”形成相互指涉的关系,而且对于理解此文本的反讽风格具有辅助性阐释的作用。反讽的定义有很多种,就作品的写作技巧而言,指言此意彼、话语表面叙述与实际表达的内涵相反的一种写作技巧,由此表达出一种谐谑、讥嘲的意味。在《阿Q正传》中,文本的反讽风格主要体现在反语的运用、反讽的结构安排以及叙述人称“我”的言行和身份反差等方面。《阿Q正传》的“序”作为进入“正文”的“门径”,其本身就在叙述中暗示了“正文”的反讽性,同时也与作品的“正文”一起构成反讽性的整体结构和氛围。
在《阿Q正传》的序中,鲁迅遵循了传统作传的套路,有条不紊地分析了立传的名目和文章的通例问题,即立传立得“名正言顺”,有名有实,传主阿Q是一个有来历、有来头的“大人物”。接着在本文的第二章及以后各章节中,叙述这个英雄的“行状”:“优胜略记”“续优胜略记”“恋爱的悲剧”“生计问题”“从中兴到末路”“革命”“不准革命”“大团圆”,从这些章节的题目中,我们仿佛看到一位历尽坎坷、但最终结局圆满的英雄。然而,在宏大的英雄叙述模式中,写的却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人物,或者说,是在平凡之下的一种人物。显然,所谓的英雄是一个假英雄。在序中看似一本正经的分析之中,却掺杂了种种不确定的因素。又因为传主的平凡无奇,连传的名字都取自“闲话休题言归正传”之中,蕴含着戏谑和正话反说的意味。同样地,正文的各章标题,看似有恢宏气势,若关照到各章内容之中,气势便轰然倒塌。所谓“记略”,不是对历史上著名的史实的叙述,而是著名的相反一极,记述的是平淡无奇甚至是有些可笑、可供嘲讽的一些小事,比如阿Q自高自大,看不起旁人,欺软怕硬,攀比惹事等事情。所谓“优胜”“革命”“大团圆”等,都可反其意来理解,在这表面的堂皇之下,皆是一些捉襟见肘的事,如所谓的“优胜”,不过是自欺欺人的“精神胜利法”。
序中论证立传名目的严肃性和实际论述中的调侃性,形成一种反讽的意味,这一方面为理解正文内容定下了反讽的基调,提供一种戏谑的解读氛围,即用与表面的叙述相反的思维来看小说中的故事;另一方面,这种戏谑味道与第二章以后“正文本”的反讽风格共同构成一个整体,形成《阿Q正传》反讽性的文本氛围。
文本的反讽性不仅体现在结构的安排上,还有语言上的显现。比如标题中的用词,所谓“中兴”,通常情况下,指的是国家层面的意义,指国家由衰退到复兴。而鲁迅将“中兴”一词用在阿Q身上,可谓是夸大了阿Q的身份地位,再联系到阿Q的“中兴”,实际上不过是做了一些偷盗之事,由此满是讽刺戏谑的味道。又如结局的“大团圆”,不是阿Q爱情之树的开花,也不是阿Q生计问题的解决,更不是阿Q革命的成功,而是阿Q之死,这与所称的“大团圆”之意义大相径庭。
阿Q的“恋爱”也不过是阿Q自己臆想的夸大化。所谓恋爱,于阿Q而言,根本就是空洞的词语存在,仅仅是“我和你困觉”⑩的本能性欲的初步表达,更不用说阿Q的“恋爱的悲剧”了。恋爱都是虚无缥缈的,又何来的悲剧呢? 同样地,所谓阿Q的“革命”,也是一种本能欲望的表现,与革命本身的严肃性完全不符。在阿Q一流的眼中,革命不过是改朝换代,换了个主子罢了。“革命”的成功,对于他们而言,仅仅意味着奴才造反成功,奴才成为了主子,意味着自己的欲望( 财欲、性欲) 能得到尽情的满足。而“革命”的行动,在阿Q们的认知中,也仅仅是“站队”和“剪辫子”一类的事。将严肃宏大的“革命”一词放在阿Q们的肤浅的理解之中,集庄严与可笑于一体,造成荒唐滑稽的效果,形成反讽的语言氛围。
“阿 Q‘先前阔’,见识高,而且‘真能做’”瑏瑡,作者在文本的叙述中,为“先前阔”“真能做”等话语加上了引号,这不能不引起注意,如果阿Q真的“先前阔”“真能做”,那叙述语言中的引号岂不是多余? 显然,这是一种反语的语言表述安排: 阿Q先前并不阔,阔,只是阿Q自己精神上的幻想; 阿Q也不是真的能做,他更不“几乎是一个‘完人’”12
此外,《阿Q正传》中叙述人称的设置也显露出一定的反讽意味。序中的叙述者是第一人称的“我”,“我”在遵循着传统的作传体例,一板一眼地寻找为阿Q作传的名目,搜寻阿Q的姓氏、籍贯、名字等身份信息。这些显然与“否正统而倡异端”13的鲁迅的行为相悖,因而可以说,是“我”而不是鲁迅,在为阿Q作传寻找名目。在服从传统的作传形式之中,隐含的是语义相反的含义。鲁迅在序中所探究的问题都是在正话反说,表面上是在为阿Q作传寻找名目,探究阿Q的姓氏和籍贯等问题,但是实际上考究来考究去,其结果竟然是关于阿Q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,均不可考,唯一能确定的只有阿Q名字中没有任何含义的“阿”字。作传人旁征博引地要证明阿Q的不朽之处,结果证明的却是阿Q的平平无奇,其中满是反讽和戏谑的味道。
再者,“我”自己声称不是一个“立言”的人,而作传讲究的是名正言顺,作传人都不能“立言”,那又何谈传主的威严、传记的名义呢? 在序中叙述者( 作传人) 声音明确,要为阿Q立传,竭力证明为阿Q作传的合理性和必然性。然而进入从第二章开始的“正文本”后,“我”隐而不见了。在“正文本”中,“我”不再引导读者做评判,而是一方面让读者与阿Q拉开距离,让读者自己处于判断的位置看阿 Q,看到阿Q的可笑之处; 另一方面,因为阿Q的无具体指涉性而让读者疑心写的是自己,从而进行自我反思。
其实,不论是在结构上的反讽,还是在人物话语、叙述话语中的反讽,其反映的都是一种文化和生存上的反讽与反思。阿Q当然不会真正地要去革命,他都不知道革命真正意味着什么,其革命的真实动机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。对于阿Q们来说,革命是另一种生存方式,他们想做主子,因为他们看到主子们可以三妻四妾,主子们拥有充足的物质。阿Q们所理解的革命全在“物质”层面而与“精神”无涉,这何尝不是更深层意义上的反讽!
鲁迅作《阿Q正传》,并不是在浅层面进行思考与批判,而是深入社会现实与人类本质中去思考问题的,他批判国民的劣根性,呼唤“个”的觉醒和团结奋斗,同时他也在反思时代、历史与现实的革命状况。
三、批判、反思与启蒙———以序观主题
《阿Q正传》中的“序”在很大程度上隐含着作品的主题。在一部作品中,“序跋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序跋者关于正文本本义和写作意图的阐释”瑏瑤。鲁迅将文本的第一章算作“序”,显然有他的意图所在,一开始就以“序”来显示出一种调侃、讽刺的态度。而鲁迅“之作此篇,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”14,以此深入“序”之后的“正文本”内部,能够体会出鲁迅“责之切”的批判,出之于“爱之深”的同情与“群之大觉”的启蒙目的,来自对国民生存状况与社会现实状况的反思,《阿Q正传》的正文本之本义也正是批判、反思与启蒙的合流。
《阿Q正传》的“序”本身就能代表鲁迅的一种批判态度。传统作传讲究名正言顺,讲究立之而传不朽,但是“我”不是一个立言的人,作传也“名不正言不顺”,传的通例与传统的立传通例也十分不符,甚至于要作传,连传主姓什么、名字如何书写、籍贯哪里也不确凿。看似遵循着传统的立传通例来为阿Q作传,却偏偏立传立得没有名目、不合通例,如此,以一种调侃的态度,显示对于传统立传体例的颠覆。此外,“以上可算是序”一句,更是在轻松调侃之中表达出十足的批判和颠覆意味。体会到“序”中的这种批判和颠覆态度,进入“正文本”,就不难理解鲁迅在“正文本”中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判。鲁迅先生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,主要体现为对阿Q的性格特征的揭示、暴露,比如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、欺软怕硬、自负自大、仗势欺人、思想封建等。此外,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揭示与批判,还体现在阿Q们对于革命的态度与认识上,阿Q认为杀革命党、杀头“好看”,阿Q所理解的革命就是释放自己的性欲,让自己的私欲得到满足。
鲁迅通过描写群像性的阿Q形象,来表达对于整个国民性的批判。当时的社会中有不少人,都是“阿 Q”,他们不知道革命到底意味着什么,以为革命就是改朝换代,换个新主子来服从,或者是“穿着崇正皇帝的素”的反清复明,要不然就以为是与他们毫不相关的新派的活动,又或者仅仅意味着剪辫子这种头发上的外在变化。鲁迅以一个先觉者的敏锐,察觉到了中国国民性格的这种愚昧无知,他写出阿Q相,并对此进行批判,但是又不仅仅在于批判,如果止于批判,只能算是无谓的牢骚。
带着“序”所体现的批判态度,进入对“正文本”的阅读与阐释之中,不难理解,鲁迅的批判并非无源。其批判是在对现实社会状况的反思中,所生出的由衷的“怒其不争”。《阿Q正传》中对革命的表现与描写,是鲁迅先生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深切感受,是对辛亥革命等历史事实的体会与反思。鲁迅不仅揭露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,而且也在深层次中揭示了导致民族的劣根性的根源,关乎中国内外,这种国民的劣根性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。
封建的统治在于维护封建帝王的权威和统治,这就忽视了人之“个人”的存在,几千年的仁义道德深入国民内心,让阿Q们深信之而力行之。因为太顽固,所以深受其荼害而不觉,这就“培育”出了阿Q们的“阿Q相”:顺从、顽固、贪婪、自欺、自负、封建……然而在特殊的历史时代,在帝国主义与外族的压迫和剥削中,我们民族被激起的不仅有反抗的意识,还有奴隶和奴隶之奴隶的顺从意识。他们苟活于封建统治者和异族的剥削与压迫之下,服从成疾,患上严重的劣根性,现出奴隶相。
阿Q们对于“革命”的认知,仅仅停留在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式的改朝换代的层面上。革命的行动于他们而言,也无非是剪不剪辫子之类的事情。认知多一些的,如小说中的阿 Q,想要脱离奴隶角色,进入主子的位置上,却始终认识不到人作为个体的“个性”的存在。所以这多出的一些认知,也只是一种“奴隶道德”的体现。
鲁迅憎恨阿Q身上的劣根性,但是“哀其不幸,怒其不争”。鲁迅“对于中国善良的质朴的底层人民,是具有无比的热爱的。他愈爱他们,对于他们所遭受的失败与失败主义的毒素便愈加憎恶、愤怒,宛如一个慈爱的母亲,对于她无辜的儿子头上长着恶疮所起的恶情感一样”16。他写出沉默的国民性的魂灵来,暴露出阿Q们的服从与奴性意识,他所要争取的是“人各有己,而群之大觉”17。
鲁迅先生用历时和现时的眼光来关照历史与现实,关注阿Q们的精神“优胜”。所谓启蒙与觉醒,是思想上、精神上的觉醒。鲁迅先生希望阿Q们觉醒、不再自欺,成为有个性、有 理想的“个”,“个”之团结一致,共同对抗侵略者的剥削。要唤起“群之大觉”,必须暴露、痛击“国民劣根性”,阿Q们必须在思想上换新,因而“首在立人”。
鲁迅在批判与反思之深处,有“哀其不幸”的同情,也有“怒其不争”的愤懑。存在,如何在反人性的环境中生存? ———“是故将生存两间,角逐列国是务,其首在立人,人立而后凡事举; 若其道术,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。”18鲁迅不仅是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者,也是新的国民性的建构者。辛亥革命时代的中国人所缺乏的,是人作为“个”的“个性”。阿Q们没有自我的意识,缺乏反抗、战斗和前进的精神,他们处在封建统治者和外族的压迫之下,麻木而妥协、顺从。
阿Q们的顺从和“精神胜利”,其后果只能是伤害了他们自己,至于压迫、剥削他们的“主子”,则不会伤到毫发。鲁迅痛定思痛,致力于改变中国国民的这种生存困境,其主张的,正是人之“个性”与“精神”的建构。
阿Q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,受着压迫和凌辱,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,生活没有基本的保障。鲁迅虽“怒其不争”,不免也“哀其不幸”,对他们抱以同情。阿Q是鲁迅所处时代各个阶层的奴隶根性的性格的集合,是具有群像特征的人物,鲁迅在《阿Q正传》中要揭示其身上的劣根性,然而其最终目的并不在暴露,而是要唤醒。如果人各有己,每个人都有反抗的意识,那么集体就会有一致对抗侵略和压迫的力量。
鲁迅思考的出发点远高于对具体环境中的国民性的观察,他是从人类生存的层面出发而反思自身存在的。因而如果要具体到中国,具体到中国的辛亥革命时期,鲁迅的这些思想足以烛照中国的前途与未来,为混沌的中国社会指明方向。鲁迅从人类、民族生存的角度出发而进行思考,阿Q们如果能够觉醒,坚持反抗与战斗,这就是“个性”的获得,而群之“个性”精神崛起,“立人”的目的也就达到了。
结 语《阿Q正传》的“序”作为进入正文文本的“门径”,一方面为我们理解正文内容提供了解读氛围,序中传主身份及文本叙述的模糊性,指涉正文文本中人物阿Q的集合概念性,序中表现出来的反叛传统的态度,暗示了正文文本的反讽风格; 另一方面“序” 也与“正文本”的叙述形成互相指涉的跨文本解读关系,“序”和“正文”表达的反讽和批判不是唯一的目的,鲁迅先生在《阿Q正传》中所显示的,还有对于历史与现实的反思,以及对于“立人”理想的追求与呼唤。对于《阿Q正传》来说,“序”是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部分,它为后面的正文文本奠定了一个基调,是理解正文文本的密钥。